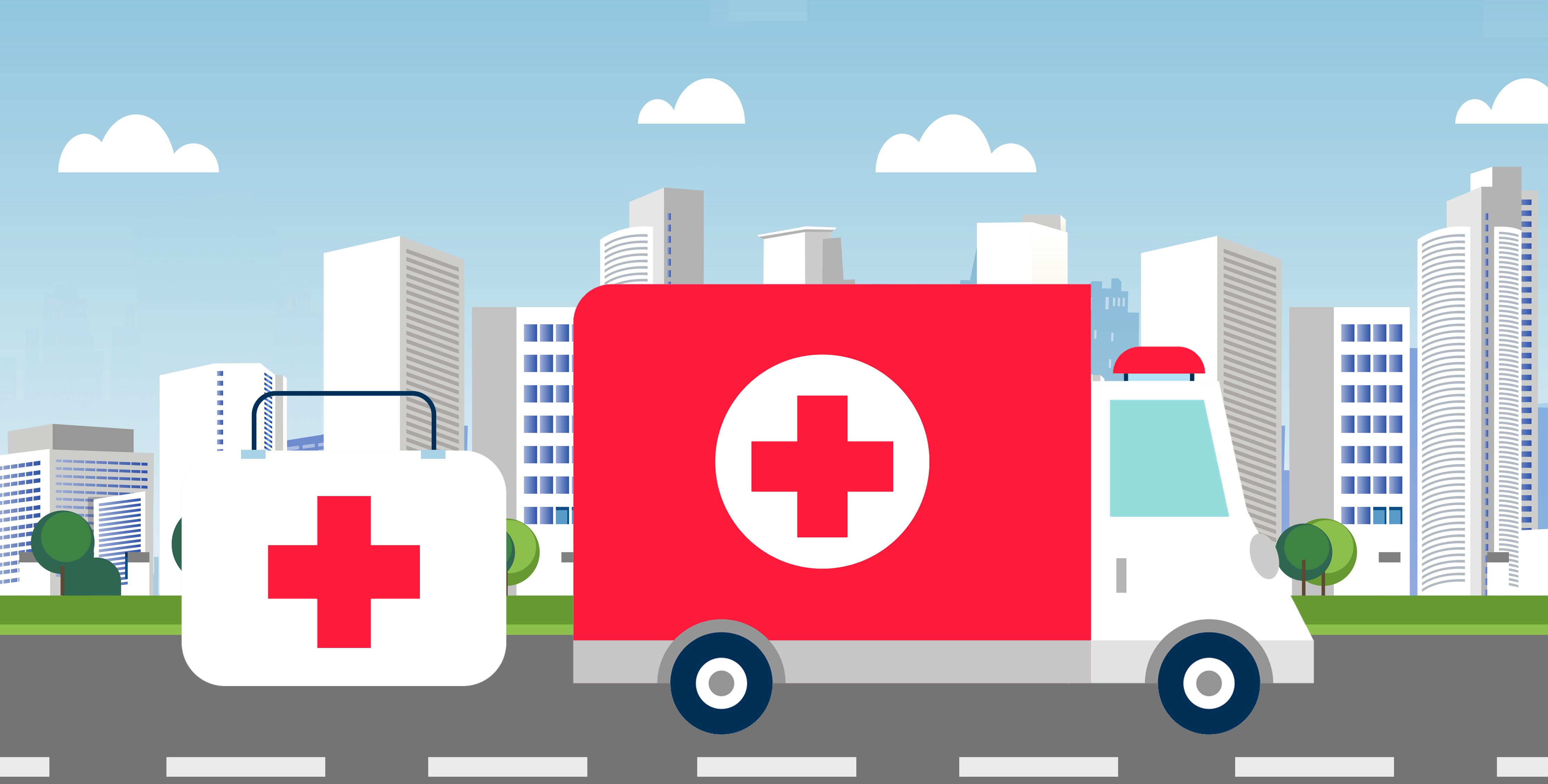新華社記者 明星 張格
東漢時期的“三聯單”長什么樣?湖南省益陽市兔子山遺址出土的3枚簡牘,形制一模一樣,內容分為兩枚“入”單和一枚“出”單,記錄了漢獻帝建安年間一次糧倉登記交糧的情況。
自2013年益陽兔子山遺址發掘以來,考古發掘領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春龍一直在對出土的簡牘進行系統性研究。近日,作為研究簡牘的專家,他披露了這一研究成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3枚簡牘出土于兔子山遺址6號井,經過清洗,兩枚為“入”單,沒有完全分切開,可以辨認出“入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 倉嗇夫文 熊受”的文字。另一枚為“出”單,可以辨認出“出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 倉嗇夫文 熊受”的文字。
經測量,每一枚簡牘長24.7厘米,寬1.1厘米,厚0.5厘米,含水重47.6克。
益陽兔子山漢簡清理發現的漢獻帝時期“三聯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據專家釋讀,“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熊”是經辦人員,“倉嗇夫文”是名字叫“文”的倉庫主管,他們共同完成并記錄了這次糧食入庫的情況。“胡盛”是接受糧食者,“掾”是他的官職,“平斛”是當時糧食稱量方式的一種。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兔子山簡牘整理工作人員楊先云介紹,這3枚簡牘出土時并不在一個層位,“入”單在6號井的第六層,“出”單在第七層,可以拼合在一起成為“三聯單”。
“從這張‘三聯單’來看,說明東漢時期益陽地區糧食管理非常規范。”張春龍說。
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史專業委員會委員陳敏副教授介紹,兔子山遺址出土的三聯單簡牘,與現代意義上的多聯式原始憑證性質相似,能滿足不同部門記賬和管理要求,并據以進行賬目核對、校驗及防止篡改舞弊等。
“三聯單”本應該分在三個地方保管,這3枚簡牘為何會同時出現在同一口井中?張春龍推測,有可能是完成對賬后不再保留。而兩枚“入”單之所以沒有分切開,有可能是同時保存在倉庫而未分開,也可能是未實際使用為憑證。
據了解,益陽兔子山漢簡6號井的簡牘整理工作,已于2018年初步完成,相關研究成果即將付印出版。